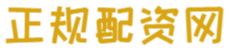在您开始阅读本文之前,诚挚邀请您点击“关注”按钮,这不仅方便您参与讨论和分享炒股十倍杠杆,也能让您体验到更丰富的互动感受,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
现今我国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夫妻之间除了常见的婆媳矛盾和夫妻间的小摩擦外,较少有复杂的人际纠纷。但回到古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的时代,情况则截然不同。除了婆媳、夫妻间的纷争外,正妻与小妾之间,甚至小妾彼此之间,还充满了各种利益纠葛。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对于那些拥有众多妻妾的古人而言,如何平衡各方关系是一大难题,一旦处理不公,家庭内部的矛盾便会激化,妻妾之间的关系自然会恶化。唐代妒妇现象的兴起,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并广泛流行的。
妒妇,实际上是古代特殊婚姻制度的产物。从狭义上讲,妒妇特指那些因丈夫迎纳小妾或丈夫行为不检而产生强烈嫉妒心的妇女,这类妇女多为富贵人家的正室妻子。她们大多出生于名门望族或家庭条件优越,自幼生活富足,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较为开明,内心渴望能在封建传统礼教的压迫下与丈夫平等相处。然而,时代的限制让她们的意愿难以施展,难以改变自身的处境。
展开剩余84%唐代妒妇现象的盛行,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大唐盛世时期,国家实力和经济高度繁荣,百姓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也随之提升。李唐王室带有鲜卑血统,受鲜卑民族文化影响,唐代社会风气较为开放,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封建礼教逐渐失去统治地位,成为妒妇现象流行的重要土壤。
正因为儒家礼教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获得空前提升。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封建王朝表面的装饰,女性权力得到实际体现。武则天称帝、韦后辅政、公主参与政务的例子层出不穷,彰显女性的地位非比寻常。在儒家思想逐步式微的背景下,唐朝统治者提倡三教并存,即儒教、佛教和道教共荣。圣历元年时朝廷曾下诏:“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生一宗。”儒家推崇男尊女卑,影响减弱;佛教强调众生平等,道教强调阴阳和谐,多元宗教信仰共同推动女性社会地位稳步上升。直到宋代三教融合,程朱理学兴起,女性意识才重新被束缚。
在唐代女性地位显著提升的同时,其婚姻制度也为妒妇现象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唐朝婚姻逐渐重视门当户对,崇尚家族门第,世家大族通婚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出现皇族欲与名门贵族联姻却被拒的尴尬局面,当时流传“李郑崔卢,姓之名器,千古推高,九流仰视”的说法,李指李唐王室,其余四姓皆为当时显赫世家。唐文宗因联姻被拒感叹:“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足见这些大姓女性地位之高。世家女子虽知书达礼,但对婚姻中爱情的占有欲及排他性极强,甚至出现倚仗家族威望凌驾于丈夫与公婆之上的强势妇女。世家通婚不仅关乎两大家族的利益,休妻更涉及复杂法律和家族荣誉,成为妒妇们权力的法律保障。
唐朝法律允许男子纳妾,尤其是正妻多年无子嗣时,纳妾被视为正常现象。尽管唐朝礼教不如以往严格,但“无后即不孝”的儒家观念深入人心,许多男子以“开枝散叶”为由,广泛纳妾,纵情享乐。唐朝并未对纳妾数量作出严格限制,致使纳妾风气盛行。纳妾标准首重年轻美貌,“纳异宠而薄糟糠,凡今众矣”,史籍中正妻被冷落为普遍现象,妒妇的产生由此不可避免。
对丈夫来说,妾不仅意味着传宗接代的责任,也带来情感的慰藉;但对正妻而言,妾则是对自己爱与财产的掠夺,更是声誉的威胁,利弊明显倾向不利。唐代法律明确妾的地位远低于正妻,正妻在法律和现实的双重落差下,妒忌心易于滋长。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已有妒妇记载,如《左传》载:“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中“妬”即妒忌之意。唐代之前,妒妇多因嫉妒他人美貌而生纷争;唐代则多以家庭内部关系为焦点。无论帝王后宫还是平民百姓,妒妇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影响朝堂政局。诗人李白由此写下“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妬杀人”这样的感叹。
自幼受宫廷斗争影响,唐朝公主多性格泼辣。《新唐书》记载唐宜城公主因驸马私养小妾而生妒忌,甚至违法对小妾施以重刑并杀害,这类事件令名门望族对皇室联姻望而却步。甚至传说中八仙之一张果因娶公主而畏惧,拒绝了唐玄宗赐婚玉真公主的旨意。
不仅贵族皇亲,普通官员家庭中的妒妇也不在少数。《北梦琐言》记载黄巢起义时,中书令王铎带小妾出征,正妻妒忌异常,追随至前线,甚至让随从打趣称“夫人从北边来,黄巢从南边来,两面夹击,岂不投降!”由此可见妒妇心态之激烈,平息难度之大。
唐代妒妇现象的猖獗,令当权者始料未及。相较于延续数百年的传统礼法,妒妇现象无疑挑战了旧有秩序,并成为社会常态。为此,唐朝统治阶级从伦理与法律两方面加强社会管理,提倡贤妻良母的女性典范,力图根除妒妇现象。
当时,唐朝政府针对妒妇问题采取了多种措施。伦理层面重视女德教育和提升丈夫地位;法律层面则出台相应惩治规定。古代社会“三从四德”成为压制妇女思想的铁律,但唐朝为治理妒妇现象,依旧将女德置于首位。长孙皇后尤为重视女德教育,曾编撰《女则》十卷,唐太宗称其可为后世女德典范。唐代关于女德的著作超过三百卷,数量远超后来宋元时代,其中不少内容专门针对妒妇现象。例如《女孝经·五刑章》中明确:“五刑之属三十而罪莫大于妬忌”,体现唐朝统治者治理妒妇的决心。
唐朝强调提升丈夫家庭地位,虽从现代视角看是对女性权利的压制,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却属无奈之举。唐律以“夫者,妇之天”为根本理论,期望丈夫顶天立地,妻子柔顺贤良。律法还严格划分妻妾等级,力求家庭尊卑分明,维护传统礼教秩序。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妒妇现象的蔓延。进入宋代,随着程朱理学兴起,妒妇现象虽偶有发生,却已不再主流。唐代妒妇现象的盛行,是封建社会不平等婚姻制度的必然结果。男权至上的体制虽然强势,但其弊端在女性身上集中显现,社会普遍将错误归咎于女性,却无力撼动时代枷锁,导致妇女成了替罪羊。
正如鲁迅先生在《关于女人》中所言:“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们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样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妒妇现象正是封建枷锁的产物,若不打破桎梏,类似问题必将反复出现。
参考文献
《旧唐书》
《资治通鉴》
《新五代史》炒股十倍杠杆
发布于:天津市